您好:中至麻将挂多少钱这款游戏是可以开挂的,软件加微信【添加图中微信】确实是有挂的,很多玩家在这款游戏中打牌都会发现很多用户的牌特别好,总是好牌,而且好像能看到其他人的牌一样。所以很多小伙伴就怀疑这款游戏是不是有挂,实际上这款游戏确实是有挂的,添加客服微信【添加图中微信】安装软件.
1.中至麻将挂多少钱 这款游戏是可以开挂的,确实是有挂的,通过添加客服微信【添加图中微信】安装这个软件.打开.
2.在"设置DD辅助功能DD微信麻将辅助工具"里.点击"开启".
3.打开工具加微信【添加图中微信】.在"设置DD新消息提醒"里.前两个选项"设置"和"连接软件"均勾选"开启".(好多人就是这一步忘记做了)
亲,这款游戏原来确实可以开挂,详细开挂教程
1、起手看牌
2、随意选牌
3、控制牌型
4、注明,就是全场,公司软件防封号、防检测、 正版软件、非诚勿扰。
2022首推。
全网独家,诚信可靠,无效果全额退款,本司推出的多功能作 弊辅助软件。软件提供了各系列的麻将与棋 牌辅助,有,型等功能。让玩家玩游戏,把把都可赢打牌。
详细了解请添加《》(加我们微)
本司针对手游进行破解,选择我们的四大理由:
1、中至麻将挂多少钱软件助手是一款功能更加强大的软件!
2、自动连接,用户只要开启软件,就会全程后台自动连接程序,无需用户时时盯着软件。
3、安全保障,使用这款软件的用户可以非常安心,绝对没有被封的危险存在。
4、打开某一个咨询客服组.点击右上角.往下拉."消息免打扰"选项.勾选"关闭"(也就是要把"群消息的提示保持在开启"的状态.这样才能触系统发底层接口)
说明:中至麻将挂多少钱 是可以开挂的,确实是有挂的,。但是开挂要下载第三方辅助软件,中至麻将挂多少钱 ,名称叫中至麻将挂多少钱 。方法如下:中至麻将挂多少钱 ,跟对方讲好价格,进行交易,购买第三方开发软件。
【央视新闻客户端】
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,权威,专业,及时,全面,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!
来源:聪明投资者
“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。”
“乔治·索罗斯的世界观与众不同,他天生就是一个市场捕猎者。但我认为,他做过最伟大的投资,就是发现了斯坦·德鲁肯米勒。”
“很多人喜欢填字游戏、打桥牌,但对我来说,投资就是最好的智力游戏。”
“投资的本质: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。”
“宏观投资的关键点之一:政策不一定要成功,只要它足够激进,市场就会剧烈反应,而那正是投资机会所在。”
“你必须相信,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你永远不知道变化什么时候会来,但你得随时准备好去应对。”
“人生中真正重要的,是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:是他们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,在你得意时提醒你别飘。”
这是去年10月现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·贝森特(Scott Bessent)在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的一场对话。时隔半年多回头看,还是很有意思。
过去三个多月,围绕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关税政策的争议持续发酵,市场波动剧烈,贸易预期反复,身为财长的贝森特一度存在感有限。但就像摩根大通CEO杰米·戴蒙对他的评价,“是个有分寸的人”。
在刚刚举行的中美经贸会谈中,作为美方代表的贝森特,显示了在核心决策圈的份量。
斯科特·贝森特在任职财长之前,是Key Square Group的CEO兼首席投资官。其40年投资生涯涵盖了两段在索罗斯基金的经历:第一阶段在斯坦·德鲁肯米勒(Stan Druckenmiller)手下工作长达10年,第二阶段则担任了索罗斯基金5年首席投资官。
在这两次任职之间,他曾创立对冲基金,随后退休,并加入Protege Partners。然而,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退休。
第二次离开索罗斯基金后,他以45亿美元的资金创立了Key Square,堪称对冲基金史上最大的启动规模之一。
这次访谈对话者是贝森特一段职业生涯的老同事,Protege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之一,特德·塞迪斯(Ted Seides)。
所以交流的过程就很过瘾,彼此熟捻,有问有答,知无不言。
贝森特早年放弃了美国海军学院的录取,改在耶鲁完成学业。在访谈中,他提到自己从吉姆·罗杰斯(Jim Rogers)处学习研究方法,从吉姆·查诺斯(Jim Chanos)了解做空逻辑,在索罗斯与德鲁肯米勒的体系中接受宏观投资训练。
对话涉及多个主题,包括非对称交易结构、仓位管理、风险判断、核心-卫星式的基金架构、以及宏观投资型对冲基金所面临的持续性挑战。
贝森特也分享了他对“市场何时会因政策转向而剧烈反应”的判断方式。比如他提到,政策本身是否成功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其路径对市场价格产生的扰动程度。
他当时还提到黄金是自己最大的头寸。嗯,今年应该大赚特赚了。
这场对话比较长,差不多1.8万字。聪明投资者(ID:Capital-nature)把全程翻译整理。耐心看,会有所获。
延伸阅读:《“对冲大神”德鲁肯米勒,最传奇的基金经理如何炼成?》
童年经历对于“想象力”的塑造
塞迪斯回到你的童年,是什么经历让你开始思考金融的?
贝森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小河镇,我们对华尔街唯一的认知就是1929年发生了一场灾难。
我父亲的财务状况属于大起大落的,他是一名房地产投资者,典型的“繁荣-崩溃”心态,结果他两次破产。
这让我从小就开始思考风险管理、资产配置和杠杆的影响。
我父亲还有一个特别之处,他拥有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科幻小说收藏——当然,这个“最大”标准可能并不高(笑)。
小时候,我在地图上指向南门二(Alpha Centauri,是半人马座的α星,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系统之一)的位置,比指向芝加哥还要熟练。因为他经常给我念这些书,我们还会一起到户外看星星。我们的邻居甚至有一个天文观测站,那是一段充满想象力的时光。
塞迪斯这种经历是如何引导你走向投资的?
贝森特我不确定它是否直接促成了我的投资兴趣,但它塑造了我的投资方法(拥有想象力)。
布鲁斯·科夫纳(Bruce Kovner)曾说过一句话(当时我们一起在做次贷交易),他说,我能想象一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,即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全国性衰退。
我能理解,这场抵押贷款危机已经渗透到整个金融系统,并且当时出现了一种相对新颖的金融工具,可以利用这种非对称回报机会。
这需要极大的想象力!
我记得有一位非常资深的抵押贷款经理走进我们的办公室,他甚至写过Wiley出版的《抵押贷款》专业书籍。他告诉我们,抵押贷款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,那时危机已经进行到一半。
结果,他的基金最终亏损100%,彻底清盘。他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,也无法预见CDO(担保债务凭证)中的这些层级会被完全清零。
跟吉姆·罗杰斯的交集
塞迪斯那你的投资生涯是如何开始的?
贝森特我发现,在人生中,许多最美好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最糟糕的事情之后。
虽然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也算不上什么灾难性事件。
当年我在耶鲁大学《耶鲁每日新闻》工作,那时候,如果你在《耶鲁每日新闻》干过,几乎可以直接进入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或《时代》杂志。
我当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成为一名记者,或者转向计算机科学。要知道,我进入耶鲁的那一年,学校刚刚从打孔卡片切换到屏幕输入系统,你会想象当时什么样的时代背景。
我竞选了《耶鲁每日新闻》的主编职位,但落选了。那之后,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,除了上课和吃饭,几乎不出来。
那是10月底。直到次年1月,我才调整心态,决定重新开始。机缘巧合之下,我去职业咨询办公室,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:
“耶鲁校友吉姆·罗杰斯招聘分析师。工作内容包括制作电子表格、买午餐、打扫卫生,甚至有沙发可供睡觉。欢迎申请。”
我投了简历,这份工作集合了我喜欢的所有元素。它很像新闻工作,需要构建叙事、做研究,同时也涉及数据分析。
我在那份工作中学会了如何做电子表格,那是一次极其宝贵的经历。
吉姆·罗杰斯是乔治·索罗斯的最初合伙人,他们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。
他们最早在布莱·施罗德(Blyth Schroeder)共事,乔治更偏向投资管理,而吉姆则负责研究分析。
我记得他们在1981年分道扬镳,之后吉姆开始管理自己的资金。所以,当时我加入的是他的家族办公室。
塞迪斯他有什么独特的投资方式?
贝森特研究,研究,还是研究。他总是说,他在寻找重大结构性变化。他的工作方式就是不断挖掘信息,验证数据。
他对我影响深远,因为他经历过60年代和70年代的市场周期。60年代是“疯涨股”时代,市场充斥着概念股,70年代则是“漂亮50”主导的市场,随后又进入了做空周期……
塞迪斯你和吉姆·罗杰斯共事了多长时间?
贝森特就几个月的时间,但我们后来一直保持联系。他曾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投资管理课程,我在耶鲁大学读大四时,每周从纽黑文往返哥大去上他的课。
1984年,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
塞迪斯你从学校毕业后,选择了什么方向?
贝森特1984年,投资银行业刚刚起飞。当时,我不太想去做那种两年期的分析师项目,因为此时我已经完全被股票市场吸引住了。
有一个叫“价值线(Value line)”的金融服务,每周会寄来一本巨大的收益报告,你可以用25美元订阅试用版。我那时候一直用不同的地址申请试用版,我的室友笑称我是“试用版猎人”。
(聪投注:Value line是很多投资大师的重要参考,包括格雷厄姆、巴菲特、彼得·林奇等等。巴菲特还说,“如果你认真阅读《价值线》并深度研究其中的公司,你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投资的机会。”)
从完全不了解股票、市场、货币,到彻底沉迷于市场,我的兴趣越来越浓。
1984年,几乎只有两家公司愿意直接从学校招投资管理岗位的人——布朗兄弟哈里曼(Brown Brothers Harriman)和弗雷德·阿尔杰(Fred Alger)。
最终,我选择了布朗兄弟哈里曼。
塞迪斯第一份工作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体验?
贝森特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,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“相对业绩”。
(聪投注:相对业绩关注的是相对市场基准的优劣,比如“本基金比标普500指数高3%”或“过去一年跑输同类基金2%”。简单来说,它衡量的是你比别人(或市场)表现得更好还是更差。)
在吉姆·罗杰斯那里,甚至在索罗斯的体系中,投资的重点都是绝对回报,即能赚多少钱?
而在这份工作里,决策往往是这样的:“这个月,我们要买福特还是通用?”“花旗银行还是摩根大通?”
虽然这份工作涉及一些不错的分析,但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。于是,我的下一步选择是加入一个沙特家族——奥莱因家族(Olayan)。
塞迪斯奥莱因家族是怎样的背景?
贝森特他们太厉害了。这家族的父辈白手起家,在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,主要是为石油行业提供供应链支持。
当时,很多中东富人给外界的印象是沉迷于奢靡生活,喜欢明星、模特,但他们完全相反。他们对商业极具兴趣,愿意与金融人士和企业家交流,真正想要学习商业知识。
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机会。
我当时是负责其家族中女儿的投资事务,至今我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。
我们的团队很小,但我们在公司里会提交13D报告(即持股超过5%的披露文件)。你能想象吗?当时我才24、25岁,却已经坐在阿曼德·哈默(Armand Hammer,西方石油公司创始人)对面,或者与当时摩根大通的路易斯·普雷斯顿(Louis Preston)对谈。
我有机会接触大量企业CEO,同时也接触到了像利昂·库普曼(Leon Cooperman)、拜伦·韦恩(Byron Wien)、瑞·达利欧(Ray Dalio) 这样的人……瑞·达利欧甚至亲自来推销他的投资通讯。
塞迪斯那在奥莱因家族工作时,你具体负责什么?
贝森特最棒的一点是,我们几乎什么都做。
我们进行研究、管理投资组合,团队中有两个人负责交易,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期权交易部。我当时在周末专门去上期权定价理论的课程,并开始涉足期权和期货交易。这让我意识到,投资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点。
奥莱因家族的投资风格高度集中,他们非常注重与管理层的关系,他们至今仍是伟大的长期投资者。
但我们可以通过杠杆和期权提高回报率,这给了我一个完整的视角去理解不同的投资方式。
1988年,加入吉姆·查诺斯的做空团队
塞迪斯你为什么决定在80年代中后期离开呢?
贝森特当时华尔街有一种“管理层早餐会”的传统,高盛或摩根士丹利会邀请某家公司管理层举办早餐会。我在这些年里结识了吉姆·查诺斯,他是著名的做空投资者。
我们并没有在耶鲁大学重叠过,就像我和吉姆·罗杰斯一样,我们是通过“耶鲁校友”这个纽带认识的。
但我发现,我们在投资问题上的思考方式非常相似。不同之处在于,吉姆·查诺斯是个悲观主义者,而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。
这让我回想起吉姆·罗杰斯的研究风格:深度研究,并验证故事的真实性。
最终,我得出了一个结论:做空策略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资产管理类别,而吉姆·查诺斯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“白鞋品牌”(原指代表常春藤文化传统的高端机构,现泛指在专业领域中历史悠久、声誉卓著、风格稳健的精英机构或人物)。
当时,大多数做空者的形象都很神秘,甚至有些像影子交易员,他们往往通过散播故事来影响市场,整个行业名声并不好。
我认为,吉姆·查诺斯完全可以改变这一现状,并打造一个更专业、更透明的做空投资机构。
而我正是他的第一位分析师,也是公司的第三名员工。
塞迪斯你是哪一年加入他的?
贝森特就在1987年股灾之后,我是在1988年9月加入的。
塞迪斯那时候做空市场是怎样的?
贝森特当时的市场机会很多,分化程度更高。那时还没有一篮子交易,市场的指数成分股也不像今天这样高度集中。但在美国证交会加强对欺诈行为的监管之前,市场确实更有刺激性。
那是一个目标丰富的市场环境,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,比如里根税改、德州石油行业的崩溃。
此外,迈克尔·米尔肯(Mike Milken)和整个德崇体系(Drexel Burnham Lambert)正在引领一轮杠杆收购驱动的资产升值周期。那是一个适合精选个股的时代。
(聪投注:德崇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具创新性、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投资银行之一, 主要业务围绕垃圾债券市场,由迈克尔·米尔肯主导,使垃圾债券成为主流融资工具。1990年因内幕交易丑闻破产。)
我在1988年加入吉姆的公司,随后,德崇支持的联合航空收购案失败,我们在一个月内赚了10%。
接着,美国储贷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。1989年和1990年是做空金融股的黄金时期,因为这一轮金融工程正逐渐走向崩溃。
塞迪斯那个时代的金融业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?
贝森特这标志着通过储贷机构(SL)进行的金融运作走到了尽头,德崇投行倒闭,而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德崇倒闭后,市场的混乱达到了顶点。而就在这场风暴的最后一幕,萨达姆·侯赛因入侵科威特,市场进一步震荡。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那时候花旗银行的股价可能从32美元跌到了4美元。
我从中学到的一点是:市场在遭遇一次极端情况时,往往会出现同样极端、但方向相反的错误反应。
例如,1989-1990年,储贷行业崩溃,需要政府出手救助。然而,美国货币监理署(OCC)的负责人克拉克(Clark)在1990年却恐慌性地执行了监管收紧,要求银行即使借款人仍在按时还款,也必须将某些空置率极高的房产按零价值计提损失。
这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“糟糕的政策”往往能创造出很好的投资机会。
塞迪斯在你加入吉姆团队的时候,市场仍然经历着痛苦调整,随后才迎来转机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你如何衡量投资的价值?
贝森特价值的关键在于,你能否持有一只最终归零的股票。当时有太多这样的机会,很多公司最终真的归零了。
以1990年为例,标普500指数可能下跌了18%-20%,但我们的基金收益却高达50%。我们所做的投资基本上涉及三个层次:
市场贝塔,即市场整体趋势;
行业趋势,即特定行业的机会;
个股回报,我们捕捉到了许多最终归零的股票。
塞迪斯从1992-1993年起,市场进入了大牛市。作为一名专注于做空的投资者,你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的?
贝森特哦,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,因为我在1991年就离开了(笑)。
塞迪斯那可真是精准的市场时机(笑)。当时你的业绩很好,是什么促使你决定离开?
贝森特我记得是在1991年1月,萨达姆·侯赛因最终入侵科威特。市场随即大幅反弹,许多资产变得极度便宜。
与此同时,我们的基金管理规模也增长迅猛。当市场下跌时,投资者涌入做空策略。
我刚加入吉姆团队时,我们的管理规模大概只有3700万美元,其中1300万美元来自合伙人基金;2500万美元来自索罗斯基金的托管账户。
但等到我离开时,规模已经增长到了5亿美元!
然而当市场开始回暖,我发现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做空标的。
有一天,我走进吉姆的办公室,说:“吉姆,我找不到任何值得做空的东西。”
他回答: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”
于是我说:“那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做点别的。”
塞迪斯那你后来呢?
贝森特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索罗斯基金的办公室里办公。
我和索罗斯的团队关系很好,于是斯坦·德鲁肯米勒在1992年邀请我加入索罗斯基金。
1992年,第一次加入索罗斯基金
塞迪斯索罗斯基金一直以全球宏观投资闻名。你如何定义这个概念?
贝森特先回顾一下索罗斯及斯坦利·德鲁肯米勒的传统,所有人最初都是个股投资者。
乔治·索罗斯最初就是一名股票投资者,他在阿诺德·布莱·施罗德公司(Arnold Bli Schroeder)工作时,投资方法就是列出10只股票,然后与客户讨论这些股票。
斯坦·德鲁肯米勒同样如此,他也是从个股研究起步的。
但不同的是,索罗斯最终发展出了反身性理论,并将市场动态的宏观层面纳入投资框架。这就是“全球宏观投资”的雏形。
如果有人说服索罗斯某个投资是个坏主意,他会立刻撤掉,然后换上新的标的。
后来,他逐步扩展到宏观投资。斯坦利·德鲁肯米勒也是一样的路径。
斯坦利当年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匹兹堡PNC银行的研究部主管。他的投资思路有点类似我在布朗兄弟哈里曼的资产配置经验,直接扔掉传统的资产配置矩阵,在70年代把40%的资金投进石油股。
斯坦利最初也是个股投资者,但我认为宏观投资渗透在一切之中。
我的风格仍然受到杜肯(Duquesne Capital)的影响,即微观驱动宏观。我们可以从企业传递的信息中获取大量洞见。
例如:我们在PCE平减指数(PCE Deflator)上做不到比别人预测更准,也没办法建立一个比领先经济指标(LEI)更好的模型。
但如果卡车运输公司告诉你,业务正在起飞,那就很值得关注;
如果家得宝表示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,那说明需求旺盛;
如果银行CEO透露信用卡坏账率正在上升,那可能是经济问题的前兆。
因此,股票投资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,同时在全球范围内,你还可以用不同的工具来实施投资策略。
塞迪斯索罗斯和斯坦利在管理资金时是如何思考的?他们是如何找到投资回报最大的机会的?
贝森特他们会从多种角度权衡投资方法。
比如,如果认为油价会上涨,那么当钻井公司股票被大幅低估时,那就买入能源股;如果期货曲线显示未来三年油价会下降,那可能意味着可以通过期货曲线来进行对冲交易。
他们关注的核心是:在整个投资组合的背景下,如何思考这些机会?
塞迪斯当有人推荐一个澳大利亚的投资机会时,风险团队可能一看数据发现,这东西和标普500的走势几乎一模一样(R2高达98%)。那你就得问了,这笔投资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好处?”
贝森特我们会关注一个核心问题:投资置信度有多高?
迈克·波伊安(Mike Boian)曾说,投资决策的关键是信心水平要超过50%的中位数。当你对某个投资越来越有信心时,就可以逐步加大仓位。
乔治·索罗斯有一句著名的话:“我只需要足够的信息来做决定。”他不是那种因为过度分析而错失机会的人。
塞迪斯那么,如何在分散投资、集中投资和高信念投资之间找到平衡?
贝森特如果你想持有高信念投资,并愿意集中持仓,那有时你可能会没有太多持仓,甚至得持有大量现金。
这在个股投资者中很常见,比如塞思·卡拉曼(Seth Klarman)就曾长期持有大量现金。你还记得我们当时一起读的《泰德·威廉姆斯的击球理论》(Ted Williams’ book on hitting)吗?
泰德·威廉姆斯被誉为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,《体育画报》(Sports Illustrated)的一名记者曾问他:“你是怎么做到的?”
他回答:“我只挥棒打好球。”
这就是投资的本质: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。
(聪投注:这一比喻同样被沃伦·巴菲特反复引用,用来说明优秀投资者如同顶级打者,并不需要每球必挥,而是在等待最理想的“甜蜜区”时果断出击。正如巴菲特所说:“投资的好处是,市场永远不会三振你。你可以等着,只挥真正的好球。”)
德鲁肯米勒如何选拔人才
塞迪斯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,你曾与许多传奇投资人共事。除了斯坦·德鲁肯米勒,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高手?
贝森特最大的感受是,你身边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人,同时团队之间高度合作,彼此信任。
比如阿梅尼奥·弗拉加(Armenio Fraga),他后来成为巴西的传奇央行行长。当阿梅尼奥告诉你“巴西市场正在发生某些变化”时,你知道他的信息是高度准确的。如果你在巴西投资了一家食品公司,或者持有铁矿石相关头寸,那么他的见解至关重要。
你不需要去反复验证他提供的信息,而是可以直接基于这些信息做决策,这种信任是无价的。
如果你是迈克尔·乔丹(Michael Jordan),你可能希望自己出手投篮。但如果你要传球给斯科蒂·皮蓬(Scottie Pippen),你也会放心,因为你知道他会处理好这个球。
塞迪斯那么,索罗斯是如何网罗这些顶尖人才的?
贝森特他并不是用传统的方式去招揽人才,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识人之道。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经验。
乔治·索罗斯的世界观与众不同,他天生就是一个“市场捕猎者”。但我认为,他做过最伟大的投资,就是发现了斯坦·德鲁肯米勒。
1988年,乔治·索罗斯把投资组合交给了斯坦·德鲁肯米勒管理,但他仍然在幕后提供意见。到了第二年,柏林墙倒塌,索罗斯开始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慈善事业,尤其是重建东欧。
斯坦真正打造了索罗斯基金的投资团队,而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段时间,真的被养刁了(那种高效、信任、专业的工作环境让我之后很难再接受平庸的团队)。
杜肯的雇佣合同只有一页纸,上面写着:“所有薪酬均由斯坦·德鲁肯米勒全权决定。”我在四年里只听说过一个人抱怨自己薪水低,可见他的薪酬体系让人无可挑剔。
塞迪斯那么,斯坦是如何找到并选拔投资团队成员的?
贝森特我称之为“足够的绳索”原则(Enough Rope Principle,一种代表“放手试错”的管理风格)。
有一位法国雕塑家曼·雷(Man Ray)创作过一座著名雕塑,它的形状类似于一个绞索,名字就叫Enough Rope(足够的绳索)。
斯坦的风格就是给人足够的自由度,有时候成功,有时候失败,但你很快就能看出谁行谁不行。
我最初在杜肯基金负责欧洲股票投资,后来在英镑贬值事件中贡献了一点洞见,这让我在团队中站稳了脚跟。
当时,我注意到英国的房贷利率是跟随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浮动的,也就是说,如果英格兰银行在周三加息,那么房贷利率在周五就会上升。 这意味着:
政府如果想通过加息来支撑英镑,实际上是在摧毁英国的房地产市场;
如果利率升得太高,英国的借贷人将无法承受,最终会拖累整个经济。
我在这笔交易上取得了一些成绩。几个月后,我去找斯坦,说:“我在管理这个投资组合,如果可以用期货对冲,那会更容易操作。”
他回答:“好啊,你可以用期货对冲。”
又过了几个月,我又去找斯坦,当时欧元尚未推出,市场上有19种不同的欧洲货币。我对他说:“这些小型市场跟随本国货币波动,那么我可以交易外汇吗?”
斯坦思考了一下,然后看着我说:“行,那你要不要也交易债券和大宗商品?”
我当时才28、29岁,就回答:“好啊,我来做。”
斯坦笑了笑,说:“很好,那就看看几个月后你还在不在公司。”
从狙击英镑和索罗斯投资哲学中学到的
塞迪斯这场学习过程最终引导你参与了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战,这可能是史上第一笔轰动全球的宏观交易。你当时就在现场,能讲讲这笔交易是如何展开的吗?
贝森特1992年5月,英国首相约翰·梅杰(John Major)宣布提前举行大选。当时市场普遍认为他会输给工党,结果他意外获胜。
英国的政治体系很有意思,如果你输了选举,你必须在24小时内搬出唐宁街10号。
所以,当时政府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,结果梅杰赢了,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,英镑大涨。
但问题在于,英镑当时被“欧洲汇率机制(ERM)”绑定在德国马克上,这是欧元诞生前的一项关键货币安排。
(聪投注:欧洲汇率机制是欧元诞生前欧洲国家之间的一种固定汇率安排。参与国家将本国货币的汇率固定在德国马克附近的小范围内波动,目的在于保持货币稳定、为未来统一货币(欧元)铺路。
英国在1990年加入ERM,但因本国经济疲弱、利率政策受限,最终在1992年被迫退出,即“黑色星期三”事件。)
英国经济在夏天开始走弱,房地产市场疲软,而德国经济则处于高增长、高通胀的环境。
两国的利率需求完全不同,但由于汇率机制,英格兰银行被迫执行德国央行的货币政策。英格兰银行必须无上限买入英镑来维持其固定汇率区间。
于是,我们意识到:这是一个“非对称押注”。最糟糕的情况下,英格兰银行最多能将我们打回2.5%;但如果它撑不住了,英镑自由浮动,我们的盈利潜力是无限的。
我们坚信数据站在我们这边,这就像是信用违约掉期(CDS)与约翰·保尔森(John Paulson)当年做的次贷交易一样,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风险回报机会。
最终,英国政府没能撑住,英镑被迫退出汇率机制,市场一片混乱,而索罗斯基金大赚10亿美元。
塞迪斯索罗斯在80年代已经多次做出重磅货币交易,而《金融炼金术》一书记录了他如何进行投资。这本书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贝森特乔治·索罗斯在1986年出版《金融炼金术》,其中有一章叫《实时实验》,是他的一本交易日志。那一年,他的基金收益超过140%。
书中记录了他如何交易货币重估、广场协议、卢浮宫协议等事件。当时市场波动巨大,单个货币对可能一夜之间变动6%,而索罗斯会在趋势确立时,将仓位加到300%。
这本书改变了我的投资生涯。它让我意识到,伟大的投资者不仅关注市场数据,更关注人们如何“错误定价”市场。
塞迪斯除了这些交易和对非对称机会的追寻,索罗斯当年还是最成功的早期投资经理孵化者之一。在索罗斯体系下,这种模式是如何运作的?
贝森特这一体系对我的投资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,也影响了我未来所希望构建的组织模式。
我们有一个小而精、高绩效的核心团队,但我们可以通过向外部投资经理配置资金来放大我们的知识优势。
可能是某位擅长成长股的投资人,也可能是专注媒体行业的专家,甚至是日本或亚洲市场的本地投资人。
当我后来执掌索罗斯基金时,我的理念是:一个优秀的投资经理应该是你愿意投资且不用担心的那类人,他们业绩优秀,你永远不需要担心接到电话,说他们的基金“出事了”。
一个伟大的投资经理,则是每年一到三次,甚至隔年才会出现一次,但每次都带来重大交易机会的人。
他可能会说:“这是一个你应该纳入核心投资组合的重大机会。”
“这笔交易我可以单独帮你设一个账户(SPV),专门用来做这个项目,方便你独立管理和控制风险。“
离开索罗斯基金,创立对冲基金
塞迪斯你在索罗斯的第一段任期结束时,团队经历了巨变,斯坦离开,你也决定离职,并创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——Bestin Capital,管理规模10亿美元。
经历了这么多后,你对自己的投资风格有何新的思考?
贝森特我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,也是我后来在投资哲学上的重大转变,就是:永远不要迎合投资者的需求,而是要坚持自己擅长的事情。
2000年,我之所以能募集10亿美元资金,是因为我向投资者承诺,不会做宏观交易。
那时候,宏观投资成了“贬义词”。
长期资本管理公司(LTCM)在1998年爆仓,而那其实不是典型的宏观交易,而是套利策略被放大到极致的失败。
一些宏观交易导致了老虎基金的亏损,而索罗斯基金也经历了一次大幅回撤。
所以,投资者当时更愿意投资长短仓股票策略。
塞迪斯你是否觉得,这种“迎合市场”让你无法真正施展自己的投资方法?
贝森特是的,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“非对称性”。
举个例子:如果我看涨石油,按之前的逻辑,我可能直接买入原油期货,这样才能完全表达交易逻辑。
但由于投资限制,我只能买石油股,然而:石油股的表现可能受限于市场分析师的定价框架,他们可能会关注远期油价曲线,导致股价没有反应。
而与此同时,原油价格本身却在上涨。
这让我意识到,如果我不能自由使用宏观工具,我的投资能力就受到了限制。
于是,我回去找投资者,说:“我要做宏观交易,如果你们不愿意,我们可以解除锁定期,你们可以赎回资金。”
结果呢?基金业绩开始好转,投资者留了下来。
但到了那个阶段,我已经工作了30多年,从9岁起就在赚钱,那时我42岁,已经获得了财务自由,我感到身心俱疲。
管理一家对冲基金,涉及两个核心部分:一是投资管理,要构建投资组合、执行交易;二是企业管理,要运营公司、管理投资者关系。
我自认为,我们团队在投资管理方面是一支A级团队,但在企业管理方面,并没有同等水平的团队。这让我始终感到焦虑。
于是,我决定退休,考虑去当教授。如果当年我没有背着一堆学生贷款,可能一开始就走学术道路了(笑)。
有一次,我和斯坦·德鲁肯米勒以及他的妻子共进晚餐,他听完后直接说:“去你的,你一年内一定会回来……你不可能不做投资。”
他是对的。
于是,我决定半退休,加入Protege Partners,转做FOF,即挑选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和他们最有信心的投资机会来组合投资。
对我来说,投资不只是为了赚钱,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保持竞争感,持续刺激我的思维。
很多人喜欢填字游戏、打桥牌,但对我来说,投资就是最好的智力游戏。
我的一位导师拜伦·韦恩(Byron Wien)曾说:“我会一直工作,直到死去。”而他确实一直工作到去世前10天。
2011年,回归索罗斯基金担任首席投资官
塞迪斯在你那段经历之后,你原本打算再创立一只基金。但就在那时,乔治·索罗斯给你打电话,邀请你重回索罗斯基金,担任最高职位。
当时,索罗斯基金的规模已经庞大,你对“管理大规模资产池”这件事有何不同的看法?
贝森特到了那时,我的思考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在宏观投资中,大规模资金不仅仅意味着更强的市场影响力,还意味着更复杂的风险管理。
我开始意识到,流动性和规模会深刻影响投资策略的执行,这不仅仅是“找到正确的交易”这么简单。
我回到索罗斯基金后,想要验证一个问题:是否可以把庞大的资金规模转化为优势,而不是业绩的负担?换句话说,如果资金没有严格的投资授权,能够快速决策,那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资产,而不是阻碍?
最终,我们做到了。
塞迪斯你是怎么实现的?
贝森特关键在于三个方面:
第一,我们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内部团队;
第二,我们调整了外部投资经理的投资组合,并向市场释放信号,表明我们欢迎新的投资想法;
第三,我们让所有投资经理知道,如果他们带来一个好机会,我们不会绕过他们,而是可以在三天内给出答复。相比之下,像黑石这样的机构,可能需要五周时间、撰写五份投资备忘录,才能送交投资委员会审批。
我们只用三天,所以那些优秀的投资经理自然找上门来了。
最终,我们形成了一个“核心-卫星”体系,核心团队负责主要投资,而外部经理则提供专业领域的交易机会。
塞迪斯当你管理着庞大的资金池,带领多个团队,同时还要面对索罗斯本人的影响力施加,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?
贝森特我是在2011年9月加入的,那时候整个债券市场,特别是欧洲债券市场正在崩溃,意大利国债仍在持续下跌。
按照计划,我应该有90天的时间熟悉公司,毕竟当时团队里有320人,其中120名投资专业人士,而很多人并不欢迎我的到来。但现实是,我在5天内就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。
当时,约翰·科尔扎因的基金被迫清盘,抛售了35亿美元的意大利国债。摩根大通给我们打电话,问是否有兴趣接手。我在一张索引卡上快速计算后,直接告诉他们,我们愿意全部接手,并立即安排回购融资。
这就是管理庞大资金池的现实,你必须果断决策。
2015年,创立Key Square Capital
塞迪斯你是如何判断自己何时该离开的?
贝森特关键因素有两个:首先是行政管理的负担是否影响了投资业绩;其次,我的职业目标一直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,不断学习,而不是被琐碎事务拖累。
投资市场不是每天都顺利,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几个月、几年都在错误的轨道上,那就该调整方向了。另外,当团队内部的核心观点开始出现分歧,特别是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变得过于消极时,这也是一个信号。
塞迪斯你创立了Key Square Capital。为什么取这个名字?
贝森特“Key Square”是国际象棋术语,指的是残局阶段的关键一格,在棋局接近尾声时,只有一个正确的走法可以决定胜负。
这正是投资的核心理念,有时候市场上只有一个真正正确的决策,它可能出现在开局,也可能出现在终局。
塞迪斯你认为象棋是投资的最佳比喻吗?
贝森特不,流动性市场更像扑克或西洋双陆棋。
投资市场存在运气成分,你必须管理手上的牌。你不知道明天以色列局势会如何,也无法提前预测中国海军包围台湾到底是在演习还是实战。你每天都会被市场抛出各种突发事件,你只能去应对,而不能提前规划所有可能的下一步。
相对而言,私募股权投资更像象棋,所有棋子都摆在棋盘上,你可以一步步计划,像J.P摩根、洛克菲勒那些金融家,他们的投资方式更接近于私募股权,而不是流动性市场。
塞迪斯你真的深入研究过象棋吗?
贝森特是的,我们请来了一位全球排名最高的女性棋手,她同时与12-13名对冲基金经理对战,我是倒数第二个被淘汰的。
她没有蒙眼对战,但赛后,她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历史性的棋局,比如1913年古巴国际象棋大师的战术。
这让我反思,投资中是否也有类似的“古典策略”?华尔街100年前的金融家,他们的策略是否与今天的私募股权投资有相似之处?
塞迪斯你最终完全拥抱了宏观投资,是因为你认为这才是最自由的投资方式?
贝森特是的,宏观投资让我真正感受到自由。
在这个领域,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,投资各种类型的资产,设计出非对称的交易结构,并根据市场状况选择最合适的工具来表达你的投资观点。
这正是我始终追求的方式,灵活、跨市场,并且高度策略化。
当时有一家做波动率交易的基金,可能以为他们在“收割我们”。因为当时日元的波动性很低,市场上标价的隐含波动率大概只有4,而他们觉得我们愿意以6的波动率买,他们就不断地把这类期权卖给我们。
我猜他们当时肯定觉得我们疯了,居然愿意以这么“贵”的价格接这些看起来“没什么波动”的日元期权。但在我看来,这笔交易背后潜藏着巨大的机会。那时候日元在78到82区间横盘,我判断它可能先涨到95,而一旦突破,就可能一路拉升到105,甚至115。
我还记得有一次,我和乔治(索罗斯)专程去了纽黑文,拜访一位我们认为掌握独家见解的日本学者。他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的名誉教授,也是托宾的学生,对凯恩斯主义研究得非常深入。他曾参与设计日本的经济政策组合框架。
我们那天共进午餐,他把整个政策逻辑和传导机制都梳理给我们听。吃饭时,乔治问他:“你觉得这个政策真的能奏效吗?”
他停顿了一下,说:“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成功,但可以肯定,它一定会引发一场市场上极其剧烈的波动。”
这正是宏观投资的关键点之一:政策不一定要成功,只要它足够激进,市场就会剧烈反应,而那正是投资机会所在。
贝森特的投资原则和方法
塞迪斯你是如何思考仓位管理的?在这种交易中,你如何调整头寸?
贝森特我一般会采取“分三次建仓”的方式,慢慢建立头寸。而是否继续加码,很多时候取决于市场当时给了你什么样的机会。
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笔波动率交易——那家基金在向我们兜售一类叫数字期权(digital options)的合约。我们知道,这类期权一旦触发就会迅速变动,因此关键在于评估当时市场给出的赔率是否值得下注。
如果我们发现,这个交易结构本身就是非对称的,也就是说,潜在收益远大于可能损失,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明确的机会。
另外,我们也会结合全年账户的盈亏情况(PL)来看。如果这一年整体表现不错,那我们就更愿意在这种有把握的交易上加码。
塞迪斯这跟传统的基本面投资方式不太一样。很多基本面投资者会认为,一个仓位该多大,取决于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有多靠谱。但你是根据实际的盈亏情况来决定加不加仓的。这种做法背后的管理逻辑是什么?
贝森特这就像沃伦·巴菲特说的那句名言:“第一条规则,不要亏钱。第二条规则,永远别忘了第一条。”
核心的想法是,你得靠赚到的钱,去换来承担更大风险的资格。
不管是玩西洋双陆棋、扑克牌还是桥牌,你下注之前一定要看清自己手上有多少筹码。
如果你带着一万美元坐到牌桌前,而这是一切家当,你下注的方式肯定跟你手上有三万美元的时候不一样。
这其实就像安妮·杜克在《思考赌注》那本书里讲的,你得根据自己的底牌和当下的资金状况来决定该冒多大风险。
塞迪斯你刚刚提到,每年年初你都会“重置筹码”,这会对投资策略带来什么影响?
贝森特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纪律。每年到了12月,我都会重新评估持仓,尤其是做货币交易的时候。
有时候你在12月的表现特别好,趋势很顺,行情也站在你这边,收益很亮眼,这时候交易员、风控团队或者其他人可能会说:“现在已经12月15日了,我们该开始减仓了。”
而我内心可能还会想:“哎呀,这波行情说不定到了1月还能继续涨。”
但回头看,每次我在年底把仓位降下来,结果几乎都是对的。因为市场总会有反向波动,过了年,情况就会变。
塞迪斯你如何在风险管理中确保即使在一个大仓位上犯错,也不会被市场淘汰?
贝森特这正是关键所在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父亲的风险管理能力很差,所以让我变得特别谨慎。如果我对风险的态度更开放,也许我今天会更富有,但也可能正是这种谨慎让我走到了今天。对我来说,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:“狼永远在门外。”
但我确实很相信EBS对风险的定义:风险=概率×严重程度。
比如我们现在在考虑中国市场时,我会问自己:有多大概率你会突然一天把所有钱都亏光?
会不会发生类似俄乌战争那样的黑天鹅事件?俄罗斯股市当时一天之内就跌了95%,这在事前是很难想象的。
所以永远都要看两个维度:概率,和严重性。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:流动性怎么衡量?你以为你有对冲,但到关键时刻,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会突然归零,原本以为能抵消风险的头寸根本不起作用。
我自己的风险控制有一条经验:你可以集中,但不能又集中、又缺乏流动性、还加杠杆。我的做法是宁愿保持流动性好,然后再适度加杠杆。
我一直尽量遵守一套纪律,比如我的投资组合中,有一部分必须能在24到72小时内撤出。
塞迪斯你职业生涯中做过两次当时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启动:第一次是Bestin Capital,规模10亿;第二次是Key Square,启动时45亿。但我们知道,宏观对冲基金特别难长期维持下去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贝森特你这个观察非常好。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拿棒球的泰德·威廉姆斯和贝比·鲁斯来做比喻。
泰德·威廉姆斯打击率高达四成,他甚至能看清棒球缝线的旋转,年复一年都表现稳定;而贝比·鲁斯就不一样了,他打击率并不高,但他擅长轰出全垒打,那种一棒定胜负、改变比赛走向的能力,持续了几十年,堪称“挥棒之王”。
很多宏观投资,更像贝比·鲁斯,而不是威廉姆斯。
问题是,投资人往往没有耐心。你哪年业绩爆了,他们蜂拥而入;之后哪年回落了,他们又一哄而散。就是这么循环往复。
我们现在算是摸索出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式。我们有一个主基金,投资人是家人、朋友和一些长期出资人,他们更看重三年维度上的表现,而不是短期波动。
有一份共同基金的研究报告指出,对于资产配置人来说,最有效的策略是:当你信任某位基金经理时,在他们大赚一两年之后,反而应该“减一点”;而他们低迷时,你反而要敢于加码。
在我过去的经验中,那些在我们表现不好时敢于加仓的投资人,最终得到的回报反而是最好的。
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跟很多大基金保持关系:我们会不定期、可能是一年一次,也可能是三年一次,向他们提出一些“特别大的投资想法”。
我们会为这种机会设立一个SPV(专项投资结构),在那个项目上加杠杆,一旦这笔机会结束,我们就把资金退回去。
未来半年到1年,市场的关注点和机会
塞迪斯我一直跟别人说,你是我认识的人里,最像能提前半年读懂报纸的人。现在你在想,接下来六到十二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?
贝森特哈,我也想夸夸你,毕竟好的同事很重要。你当年给我的提醒就很中肯,我有时候看得很准,却没有建立仓位。你能一针见血地将这点指出来,对我帮助很大。
(聪投注:前面贝森特讲过在尚未回归索罗斯基金之前,曾加入了Protege Partners,而当时特德·塞迪斯是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,他曾于2002年共同创办Protege Partners,并担任投资负责人多年)。
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:如果我真能提前拿到“未来六个月的报纸”,我真的能一眼看出该怎么做交易吗?
比如:如果有人告诉你,“以色列的战争还会持续一年”,但油价却会更低,你会知道该怎么做吗?其实也未必。
这类结论并不是直觉上那么显而易见的。
我们现在面临一个7%的财政赤字。在传统理解中,这种情况下利率应该会大幅上升,但我们却看到所谓的“华丽七巨头”大涨,科技板块也在形成泡沫。
所以,关键不只是判断会发生什么,还要考虑未来新闻头条可能写什么内容,以及你选择的投资工具是否合适。
我认为,接下来几个月的市场走向,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美国大选的结果。
如果最终是共和党胜出(我希望如此),同时拿下总统、参议院和众议院(即“三权全掌”),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增长冲击,市场情绪会明显回暖。
而这时候,美联储此前的“超级降息”(2024年9月份)可能就被证明是错误的。我希望他们不要被迫再加息,否则会严重损害联储的信誉。
另一种情况是,如果副总统哈里斯当选,那么大概率会形成一个分裂政府(总统归民主党、国会归共和党)。共和党可能拿下参议院,而我们依然要面对这个持续扩大的7%财政赤字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。
我强烈的感觉是,中国现在采取了一些短期战术动作来稳定经济。但其领导人跟过去我们熟悉的中国领导人是完全不同的类型,过去十多年,中国实行的是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”或“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共产主义”。
再说回市场,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轮黄金的长期牛市之中。我们能看到各国央行正在不断增加黄金储备。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一趋势,黄金也是我当前最大的头寸。
就连我自己前几天也被波兰央行的公告惊到:他们表示希望把黄金储备占比提高到20%。
在我职业生涯中,有些最成功的投资,都是出现在这种情形下:当一个政府、一个管理层或一项政策正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冲向一堵墙,你通常会假设他们会踩刹车转向。而这种政策转向,就是我们最大的投资机会来源。
当然,也有几次,我亲身在车上,结果他们真的撞上去了,那就不太好受了(笑)。
但总的来看,我做得最成功的几笔投资,都是在提前察觉到即将发生的政策转变的时候。
有句里根时代白宫里的话我很喜欢:“政策就是人事,人事就是政策。”
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政府官员,说到底都是人。他们希望被人认可;如果是民选官员,他们还要考虑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。所以,他们其实很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。
只要你长期关注他们、保持持续对话,其实是可以察觉出,他们什么时候真的准备踩下刹车。
而这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风险控制手段。因为往往当系统已经失衡到极致的时候,你反而能找到特别好的入场点。
塞迪斯那除了中国之外,你现在还有特别关注哪个市场?
贝森特我特别关注日本。我认为那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牛市,是当前全球市场中少数几个值得关注的长期机会之一。
安倍当时的政策非常好,同时也带来了稳定性。可惜的是,他遇刺时了,否则我相信他还有机会回归。现在的日本政坛可能又要回到那种首相轮流坐庄、频繁更换的局面。
至于欧洲,那边情况更复杂,我觉得在政策、去工业化进程,尤其是政治层面,都是一大问号。
我预测在接下来的18到24个月内,玛丽娜·勒庞(Marine Le Pen)将成为法国总统。因为左派的候选人实在太弱,选民反而觉得她更现实些。
欧洲现在的民粹政治浪潮,一方面是对贸易和移民的反弹,另一方面其实也和欧洲自身一系列错误决策有关。
看看德国的产业政策吧:他们选择继续把商品出口到中国;继续依赖俄罗斯的能源;为了照顾南欧国家而维持一个低汇率;关闭核电站,让自己更加依赖俄罗斯能源……
而现在,反倒是南欧国家的经济表现比德国还要好。我很想看看,接下来的几年,德国这个庞大的工业出口机器会如何应对这种格局转变。
塞迪斯我知道你多年来一直是个非常低调的人,而最近,你被点名为如果特朗普当选后可能担任公职的人选之一。我想先问一个问题:你是如何区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你的投资职责的?
贝森特这是个好问题。在我管理的基金里,我始终坚持一点,市场里不该有狂热分子。
我现在所做的很多事,其实就是我过去35年一直在做的:地缘政治分析、宏观经济分析、趋势研究。
我之所以选择不再躲在办公桌后面,是因为我真心认为,这次选举将是一个关键的抉择。它将决定我们国家是否还能靠增长来摆脱债务负担。
而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:通过放松监管、能源独立、强化美国的主导地位,再加上一个真正以增长为导向的思维,我们是有机会走出困境的。
我非常坚定地认为,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靠增长化解危机的机会。我也相信,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重组的中间阶段,在全球政策和全球贸易层面,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再造。
这其实是我当年在耶鲁教过、也是我一生都在研究的东西。我希望能参与其中,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。
第三点,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组后的共和党,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政党。它是一个工人阶级和商业阶层融合的新联盟。
我很在意这些新选民能否被好好对待。
我自己小时候,家庭条件很不错,但后来父亲的失败让我们一度失去一切。如今我重新站了起来,所以我对经济焦虑这种感觉是有切身体会的。
我希望这些人群,尤其是普通劳动者,未来的生活能真正好起来。
塞迪斯这次访谈播出时,大概率两个党派中会有一个胜出。如果特朗普赢了,你会去做什么?
贝森特我现在所做的一切,就是为了确保他能赢。如果他输了,那我没有其他计划,一切止于11月5日。
关于人生,一些重要的问题
塞迪斯好,那我想问几个轻松一点的问题。除了工作和家庭,你现在最喜欢的爱好是什么?
贝森特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变了。我记得我们之前共事那会儿,我还在做铁人三项。
我要提醒大家一句,如果你正经历中年危机,千万别去搞铁人三项——我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工髋关节(笑)。
现在我重新找回自己喜欢的休闲方式,倾向于做一些适合长期坚持的运动,比如远足、散步或者打高尔夫。
塞迪斯有没有什么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?
贝森特可能20年前我会选择从政或者参军。只是……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,生得太早了。
塞迪斯那你觉得,身为同性恋这件事,对你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有影响吗?
贝森特影响很大。
1980年,那年我拿到了美国海军学院的录取通知,那是一条免费读书的路子,我们当时已经没钱了。但我最终没去,而是选择了耶鲁。
耶鲁对我很好,我打了三份工,暑假也在工作,最后熬过来了。也许潜意识里,我选择进入资产管理行业,是因为这里更公平,数字就是数字。
这不是个销售行业,你不需要靠住在格林威治、在乡村俱乐部混圈子来拿到客户的委托。我一直觉得,你的盈亏(PL)才是最好的保护伞。
如果还能补充一点的话,我可能是你见过的最量化的人,但同时也是最信教、最迷信的人之一。
我不觉得这两者是矛盾的,虽然很多人会这么看。我会祷告,也随身带着一只兔脚(象征幸运),希望我的量化模型是对的。
塞迪斯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?
贝森特特权感。我不反对有人拥有资源或出身好,但只要一个人表现出那种“理所当然”的态度,我就会特别反感。
塞迪斯哪两个人对你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?
贝森特斯坦·德鲁肯米勒,他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人,从没亏过一年。但他不仅是个顶级投资人,还是个很棒的导师、家人角色、也是一个真正有慈善心的人。
还有就是拜伦·韦恩(长期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投资策略师,并在退休后加入黑石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和资深顾问,他最广为人知的传统是每年发布“十大意外预测,列出那些市场普遍低估但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事件)。
他没有孩子,但他把我们这一代人当成自己的学生。他指导我们,批评我们,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传承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2016年那次大选,特朗普当选后的第十天,我和拜伦一起吃午饭。我问他怎么看。
他说:“我先告诉你我的政治立场,特朗普赢了那天晚上我哭了。但我现在觉得,市场要涨疯了。”谁能做到这样?!(只能说,情感归情感,判断归判断。这就是投资的境界。)
塞迪斯你人生中听过的最好的一条建议是什么?
贝森特你必须相信,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你永远不知道变化什么时候会来,但你得随时准备好去应对。
你还得准备好“撞上好运”,也就是说,如果你事先做足了准备,一旦那个关键事件真的出现了,你就能把握住。
还有一点是,我从不为短期赚钱去做事。我总是在想,从长远看,这件事是否值得投入?是否让我持续有热情?
而且,很多时候真正的大金矿,其实都藏得比较远。
塞迪斯你人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?哪件事是你希望自己早一点明白的?
贝森特长期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
我有一个大学室友,我们从17岁认识到现在,经历了彼此的婚姻、离婚、孩子出生……这些贯穿一生的朋友和关系,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
你之前问我,重新回到索罗斯基金是什么感觉?我那时候是整个212区最受欢迎的人(笑)。
甚至我在2005年退休时,还有像ISI的埃德·海曼(Ed Hyman)这样的人对我说:“斯科特,我们会把你留在邮件列表里,因为聪明人从不会真正消失。”
现在,我每天还和斯坦·德鲁肯米勒通电话,也还在和尼科·罗迪蒂(Nico Roditi,以高胜率的宏观交易著称,是索罗斯团队中极少公开露面、但内部极度信赖的核心人物之一)保持联系。
所以当我成为57街(纽约投资界)的焦点人物时,我明白,那些浮华的热度其实并不重要。真正重要的,是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:是他们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,在你得意时提醒你别飘。
我们一起共事时,你也做到了这一点,我希望我也曾为你做到同样的事。
说到底,人生的关键是:保持平衡,身边有一群能让你保持冷静和清醒的人。
塞迪斯确实如此。斯科特,太感谢你今天的分享,也祝你接下来无论走向哪里,都顺利如愿。
贝森特谢谢你,特德。
本文来自作者[一条小荷紫]投稿,不代表飞流互动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exlove.cn/zsfx/202505-2961.html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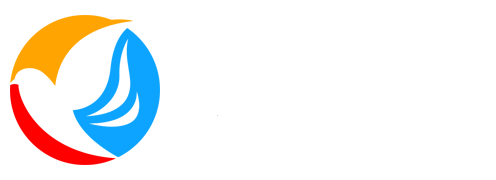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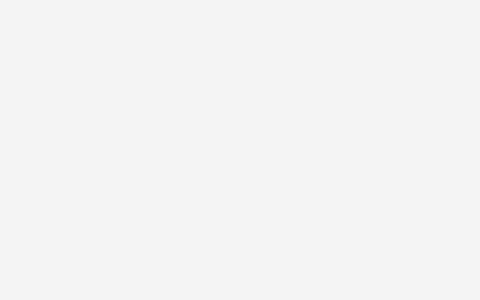
评论列表(4条)
我是飞流互动的签约作者“一条小荷紫”!
希望本篇文章《今日热议“中至麻将挂多少钱”的确是有挂》能对你有所帮助!
本站[飞流互动]内容主要涵盖:国足,欧洲杯,世界杯,篮球,欧冠,亚冠,英超,足球,综合体育
本文概览:您好:中至麻将挂多少钱...